【长,慎入慎入~!】 闲追忆 萱草种北堂

- youyou1235 LV.连长
- 2015/8/31 7:41:40
1】
上周四中午在报社饭堂和吴笋笋一起吃饭时,他突然说了一句,“不如你提前结束实习吧?”
我被吓得差点呛住,自觉实习这近两月来一直兢兢战战,勤勤恳恳,怎么突然就被抛弃了。不免朝他怒瞪,委屈又气势汹汹地问,为啥!
他正吃着一口饭,边笑,丢我一个稍安勿躁的眼神,然后解释:
“我觉得你该学的都学得差不多了,多一星期和少一星期都没什么区别了。”
“最近中院也没什么案子,现在是媒体的淡季,还不如用这一星期时间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比其他人都要优秀,所以才让你提前结束实习,要是别的实习生,本着负责的原则我都不会这样决定……”这个回答还比较令人满意,我神色稍霁。
虽然早知会有这一天,但分离是来临得如此突然,仍不免令人难以接受。吃饭过后,我一直恹恹不乐,是吴笋笋怎样安慰,是半真半假地逼着他要时时怀念我,都无法冲散心头的惆怅和不舍。
周五是实习的最后一天,但我没去中院,睡到中午起床直接去医院看病。正想着还没和一起跑中院线的几个其他报社的实习生道别,就收到吴笋笋发来的信息,“余同学,她们都很想念你。”当下心里五味杂全,几乎要哭出来。
下午在医院里接到电话,吴笋笋问我病情怎么样,我哭丧着声音说去中三三院看了口腔外科,不过感觉不靠谱,也许该去骨科。回报社后,他听到我描述“连吃苹果啊烤玉米啊都不行!嘴巴张不开那么大!”时,笑得不行,好像是自从我嘲笑他前女友说他虚伪后,头一次逮着机会报复,连说对我这个吃货来说真是悲剧。不过,笑归笑,还是很认真地帮我查医院,咨询报社里跑医疗线的记者,最后确定了一家空军的部队医院后,“我周六陪你一起去吧。”
晚上,楼上编辑部的一位元老级编辑要离职,关老师决定叫上平时相熟的编辑,一起吃饭送行,我抛弃和吴笋笋照例的晚饭时间,跟着一起去了。
席上只得我一个实习生,不过好在同行的编辑即便和我不熟,也至少混了个脸熟。关老师总拿我当小孩子,哦不,是他们楼上编辑部都拿我当小孩,编辑部一向不招实习生,几年了只见我一个楼下采访中心的实习生上来,天天晚上上蹿下跳,不是和这个责编学习改稿,就是和那个美编学习排版。他们给元老践行,其实我也就是去蹭饭的,不停动嘴巴,吃得不亦乐乎。
回去时夜色温柔,我和元老走在最后,吹着晚风,听他说着将来的一些打算,心下却浮起了一层浅浅的惆怅。元老五年前从上海来到广州,是看中了广州的媒体环境,如今却又离职返回上海,五年兜兜转转,回到原点,但人事皆已不同。突然就想起茨威格在成名之前,身上钱财只够在维也纳租一间小小的斗室,三十年后,他受政治牵连,家财声望俱不可求,重新回到维也纳,租了一间和当年一般大小的斗室,隐姓埋名低调生活。人依旧,房依旧,心境和状况却天翻地覆,“五十多岁的我再次面临人生的一个开端,重新像一个坐在书桌前的学生,早晨疾步走到图书馆去——只不过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淡淡的沮丧。”
我慢慢走神,未来的我又会在哪里呢,想做的事情是那么多,却每一件都难,我多希望自己能够坚强如初,一直勇往直前,达成心愿啊!
2】
来报社实习的第一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后来事实证明,真的是太早了。七点到报社,整个采访中心只有我一个人……
当时初来咋到,心里不免忐忑,对着一栋楼发呆,不知该去哪层楼哪间办公室找推荐人陈主任,打电话没人接,后来知道对方压根就还没起床……
徘徊了十多分钟,终于在一楼楼梯前逮着了个人影,是个很年轻的男子。不过我问得心里没底,他听着也莫名其妙,在得到我一连串的“不知道”后,他沉吟了下,建议我,“若是从编辑部开始,那就至少是4楼以上。”这个回答已经好太多了,我兴高采烈地道谢,他见我突然灿烂一笑,一愣,也笑了。两个月后的今天,我都没忘记这个笑容,它安抚了我当时因找不到方向而焦躁不安的心。
直到实习结束,天天在报社进出的我,也没有再见过这个人了。
中午时,我才见到要在未来两个月里带我的记者。我正坐他位置上帮新认识的别部门的实习生打名片,那个可怜的孩子,已经连着干了一星期了,把名片转化为电子版,还必须特别小心翼翼不出错,以至于在我礼貌地问“需要我帮忙吗”时,连客气都不讲,只犹豫了一秒就双眼泛泪花地握住我的双手欢呼,“太好了!”
吴笋笋风尘仆仆地走进来,我抬起头时,他正面无表情地盯着我,着实把我吓着了。他一板一眼地问,“你在干嘛呢”,我也就一板一眼地回答,“帮实习生打名片”。他扭头朝别的记者问,“谁让实习生干这么缺德的事情啊”,我默了一下,这人连说笑都这么冷吗,真可怕……
后来和他了解熟悉后,才知道他当时是有笑的,只不过嘴巴上扬弧度细微得几乎不可察觉,简而言之就是腹黑。
我来的时机不巧,那时正好是广美副教授案的后续结束工作,对这个大案子我只来得及贡献下我的整理录音能力,不过第一天晚上我就和吴笋笋一起上编辑部看着编辑排版了。说来,我是先问了当晚做这版的编辑是谁,然后自己上楼找那个责编关老师。上去时,关老师正皱着眉头一脸严肃加不耐烦的样子,我瑟缩了下,心里先预料自己会被拒绝。恰好又有图编来找他商量用图的事。等到他们聊完了,关老师看向我,语气颇温柔地问什么事,也就是那一刻突然镇定下来,不过是提出自己的一个请求罢了。
在他得知我想跟着看版后,倒也很爽快地答应了,不过还没到改这篇稿子的时间,关老师遂说,“你先下去吧,到了我会下楼找你。”
我本不抱着太大希望,不料到了十点半,果然见到他风风火火地下楼,叫我上去看他改稿,那刹那心里涌现的感动是无法言喻的。报社的实习生如潮汐般来了一批又一批,数目多得由不得老师去记住名字,在之前就听闻了太多报社中人对实习生的态度后,我深知别人对自己好很难得。
后来,在我和关老师熟悉后可以互开玩笑,蹭吃蹭喝后,我曾发信息问他当时得知我的请求后心里是怎么想的,会不会很惊讶。他说,是不习惯,回想当时,真可以婉拒你,不过幸亏没那么做,现在觉得你是天赐的一份礼物。
我亦很庆幸能遇到这样的人。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亦觉得当时的请求有些强人所难。上夜班的编辑工作很辛苦也很紧张,更没有人会习惯在工作时旁边有人盯着。同是编辑的陈老师也曾笑着问我,看他改稿时是不是一直皱着眉头的。我有时上去,一眼望去,这六个责编竟齐刷刷地皱着眉紧盯电脑。而关老师,也是在我跟了一星期后才慢慢习惯。此刻写到这里,感觉心里诸多歉意。
许是太显眼,不过两三天,就已经被大半编辑部的人听闻,有些人,在我还不认识时就已经叫出了我的名字,我这样的举动延伸到将来细想起也是会毁誉参半吧。我不是个喜欢高调的人,甚至很多时候不善交际,但行动之前常常自问是否出于本心,若是,便会不计后果去做,因此常常显得显眼,更常常得到误解,你觉得我别有用心,但我反认为你心思太重。后来,某次和关老师聊到办公室文化时,他说,你太显眼了,容易被人作为靶子利用。我也一笑置之,若是那样也无可避免,我不想为了这些未知的遭遇而改变我的本性。他神色之间颇有不赞同,似觉得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3】
原先和我一样跟着吴笋笋的,还有另一个暨大的实习生。在我来了几天后,她就走了,说是找到了别的实习单位。我是那天晚上从编辑部回来后才得知这个消息的。
那天白天的实习经历其实并不愉快,我头一次单独去中级法院,但并没有拿到起诉书,也没有录音,说来也是自己以为不用写稿,遂发懒。回来后,吴笋笋很冷静地反问我,没有起诉书又没有录音,你打算如何写稿?他的语气很平淡,并无责怪之意,只是简简单单地这么问我,我却被羞愧得无地自容,在他的注视下低头不语,几乎想要退后。
他见我不答,摆摆手说没事,然后开始工作。我在旁边站了近两小时,不敢动更不想动,后来他发现我还站在他身边,问我,怎么了,我才讷讷地憋出一句话,我保证下次会做得更好。
似乎近两小时的纹丝不动,近两小时的不安和愧疚还有自责,都无法找到确切的语言表达,而说出口的这句保证,只不过是最单薄的形容。
晚上收拾东西准备下班时,吴笋笋突然对我说,“王涵走了,所以你要好好努力啊。”他的语气很轻松,还带着笑意,但是我却感觉这是他头一次这么认真地对我提出一个要求。王涵走了,也就意味着他只剩下我一个实习生。
我们一起走出报社,他不放心我晚归,带着我一起打的,送我到地铁口。在车上,他第一次说了这几天观察下来对我的评价,以及他对实习生的要求。我坐在后座,把脸贴在前面冰冷的铁管上想听得更清楚,车里冷气很足,我冻得有些发抖,他的话一字一句地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心里既有对白天那件事的愧疚,又有面对接来下状况的期待和担忧。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跟着吴笋笋跑中级法院听案子,和律师和法院书记员打交道,写稿。大约两个星期后,我已能够单独去了,从最开始面对律师时语气中显而易见的小心和紧张,到后来大致能够做到进退有度应对有章法,每天亦是六点起床赶公车地铁,晚上十点从编辑部出来下班。
每天晚上坐公车回校,远远地看到高架桥那边一溜儿起的橙黄路灯时,就觉得心情重新变得舒畅而平静。路上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影子被拖得很长,夜风轻柔,忙碌起来时会怀念上学时晚上和好友躺在桥上边喝饮料边聊天的情景,那时总觉得时间又漫长又迅速,怀着略微茫然的心情勇往直前,这种感觉很令人不舍。
4】
跑中院线的同城五家媒体中,我和易旭、贝佳、李昕、庆梅、嘉恩几个实习生是天天都要聚首的。
易旭是羊晚的,贝佳是南都的,李昕是信息时报的,庆梅是广日的,嘉恩和我都是跟着吴笋笋,她是在我来了大概一个月后再来的第二个实习生。
我们天天早上九点左右到位于仓边路的广州市中级法院,一起坐在长椅上等着开庭,边说笑和聊各报社八卦来打发睡意。一看到提着公文包的律师走进来,便上去巧妙询问案情,通过话语揣测其对记者的态度,有时不免要伪造身份,曾装作是学法律的大学生来感受法庭气氛,哄得对方拿出起诉书;也曾以正经八百的记者身份与之交涉,只是要维持专业程度令我很吃力,那时便格外渴望之前能多学些东西;也有趁律师不在时,上去偷拍资料,这种行径只做过一次,胆战心惊,还能勉强不手抖。
有时律师不好打交道,就要从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或者家属那边下手。我觉得和家属打交道最难,首先要从他们的对话中判断出是被告方还是被害方,对这两种人得说不同的话,说错了一句都全盘皆输。偏偏来打官司的都不是说正经的普通话的!一口家乡话听着跟鸟语似的,这时就只能从神态上,和律师的交流等细微方面来判断了。他们往往还很精明,一眼就看出你是记者,从眼神到动作都十分的紧惕,就像难以攻破的古堡围墙。
我试过磨破嘴皮说了半个小时,最后一句话使对方松动的,也试过一句话毁得对方立刻翻脸不愿理我。
天天都有凶杀案,但案情有曲折离奇和简单明了之分。情节复杂的,手法残忍的,我们几个就听得很精神,但若是简单没什么亮点的,就会听得让人直打瞌睡。有时我一回头,后面一排五人有三人在用低头掩饰睡觉。不过有时也会遇上有吐槽点的案件,之前有个吧,是工地里两队人打群架,有一人被另一人追着用钢筋啊,铁管啊,甚至砖头啊,敲过打过都没事,还跑得特机灵,结果他被追打得无可奈何了,反身拾起地上的一块方木朝那人头上一敲,竟就把那人给敲死了。我们写这案子时,嘉恩评论了句,“钢筋铁管不敌方木一敲”,笑抽了一天。又有一次,是情杀,一个男的把他女友给杀了,这男的妻子也在家属席上,她原本是满脸哀戚的,结果听到自己丈夫有一个同居情人不说,还杀了一个有暧昧关系的女友,在逃亡期间又有另一个女伴,我们估计她原先对丈夫的情感世界一无所知,所以听到最后她都懵了,我们一个劲感慨遇人不淑后果严重。
若遇上法庭没人,其他案子又没开庭时,我们几个会弄模拟法庭,易旭往往是扮被告的那个,没办法,他长得就像被告……李昕喜欢立刻拍照留恋,庆梅和嘉恩总是一副同性恋的样子粘在一起,而一点点小事,就能让我和贝佳在旁边笑抽。
有时几个人站在窗边说笑,笑声惊动书记员出来气势汹汹地骂人,我们再一脸无辜地望着她任由她说完,等她回到法庭上后又忍不住笑。不过当着家属面才不敢笑,要互相提醒对方矜持住,之前就见过有被告家属无意中一笑,被被害家属看见几乎要殴打起来的。
大家都是第一次实习,轻松总是多过严肃,猎奇也大于人文关怀。
现在,嘉恩和易旭都结束实习了,我也走了,南都也有了新的实习生,贝佳慢慢很少来了。没有一场筵席可以永不散场,也没有一刻时光可以永远停留,但再回忆起来,我眼前还是会浮现出当时的情景——
身材修长的嘉恩倚着栏杆,庆梅在旁边笑嘻嘻地望着她,李昕双手抱胸,不时冒出一些让人捧腹大笑的话,易旭永远都是那套白衬衣蓝外套加牛仔裤,眯着细长眼睛很奸诈的样子,我则没骨头似的靠在贝佳身上笑。旁边,是吴笋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不时拍照说什么明日之星,庆梅的老师长得年轻,笑点奇低无比,说着话自己就会突然“咯咯”笑起来,而易旭的老师黑衣黑裤,身子笔挺,生就一副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样,后来这点被吴笋笋嘲笑是腹黑,我斜他一眼反驳,你这种才叫腹黑!
我多怀念那时一起等待开庭的日子啊。
5】
没来得及和她们告别,没来得及正式地和编辑部相熟的编辑说声再见,更没来得及当面感谢吴笋笋,头一次长时间实习就遇上这样一个面冷心热的好老师……一切都没来得及,我就已经离开了。
太多话,当面说会不好意思,写下来又觉得矫情,如眼下这般诉诸笔端的,也深知只是记录那一段时光而已。也越来越明白,太多话语难以说出口,太多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如果能够以心易心,无需开口就能让对方准确无误地明白自己的心意就好了。
走时才觉得不舍,甚至连偶尔晚饭时吴笋笋抢我的菜这一情景如今回忆起来都忍不住笑,熟悉后我也总是肆无忌惮地欺诈他,在外面点餐时若是有两种主食我都想吃,就会自己点一份,再逼他点另一份,然后上来后分掉他的一半分量。走之前我曾开玩笑地说,“没有我再这样聒噪说话,再在洗手后把水珠甩到你脖子上,再在点菜时逼你点哪样哪样,再在见到你时大叫着扑过来,老师你要怀念我啊。”吴笋笋也会有一小段时间不习惯吧,曾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吃饭时一直不说话,他瞥了我好几眼,想方设法问我原因,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说,姑娘你说说话吧,我好不习惯啊。我当时笑,说你这人真是,我说话时嫌我吵,我安静时又嫌我闷。
就连昨天最后离开时,还不忘逼着他记得以后遇到大案子时把我叫上,逃课也要去经历一次大案子的完整的采写过程。他安慰了好久,以后没课时也可以过来看他啊。我却总觉得缺了什么,是不同的。
今天又去医院看病,接过吴笋笋的电话详细报告了病情后,我犹豫了好久,还是决定下周不去报社了,原先结束了他这边的实习,还可以去周刊部和编辑部继续实习,都是平时里熟悉的。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回家,过一个星期的暑假。
我发信息给吴笋笋,“老师,我决定回家了。”
他想必是笑着的,“好,回家后记着要好好休息。”
再见。
后记:
好久没写文了……感慨下……
这篇写得比较长,本就是抱着记录的心,希望以后回忆起来时还可以看看,所以写详细些。
不过有些令我感动的小段子还是没有写出来,是比较琐碎的生活片段,就让那些留在我心里就好了。
实习这些日子来,几乎没有不开心的事情,唯一一次哭得很伤心的,还是因为自己闹别扭,看到自己稿子和别人的稿子之间的差距,不知怎的一出报社就开始哭了。我收获了很多,经验什么的是一方面,但更多的是友谊和温暖,吴笋笋带来的,楼上相熟的编辑带来的,其他报社的实习生带来的。足够多了,并不因我结束实习就结束了。所以,沮丧,不舍,是有,但不会太难过。
好啦,开开心心回家过暑假。

- 粉兔小店
- 2015/8/31 12:05:54
已阅,lz再见

- goldenft
- 2015/9/1 4:44:07
通过手机
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总是好的。还有一周好好跟家人过~
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总是好的。还有一周好好跟家人过~

- tylll
- 2015/9/1 20:56:08
细腻的文字,即便是记录却也写得足够煽情了。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其实习惯了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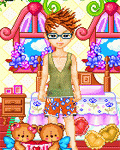
- yangrong
- 2015/9/2 13:03:01
看题目还以为是推荐什么书。。。。。
哎
哎

- linlong17
- 2015/9/3 1:32:30
辛苦了,你该回家过上一周悠闲的假期了。
喜欢看见你微笑的样子。
喜欢看见你微笑的样子。

- 晓晓溪
- 2015/9/3 12:29:41
工作中出现个小姑凉什么的的确能够增加点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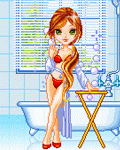
- 21059500
- 2015/9/4 7:00:42
真不错啊

- hana1414
- 2015/9/4 20:59:25
真的是很好的经历啊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