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袁氏當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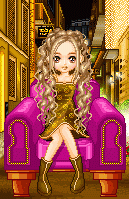
- coomady LV.连长
- 2013/6/28 10:54:20
我讀《袁氏當國》
初讀《袁氏當國》這本書,總覺得讀起來怪怪的,很不習慣,可能是因為這本書是文言文與白話文的結合體吧。本書詳細地概述了袁氏當國的由始至終,也是中華一段從“帝制”轉入“民治”的過度階段的必然的歷史。
民初的清王朝正在垂死掙扎中,而革命形勢卻是如日沖天,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在革命的a打擊下已經是搖搖欲墜了。此時的袁世凱,正處於歷史之秤的中間,無論他偏向哪一邊都可能發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這秤的一端是“帝制”,一端是“民治”,袁世凱站在這兩者之間,中華今後的歷史究竟何去何從似乎就在他的一念之間了。
袁世凱,是何許人物?
在以前的教材中,對袁世凱的評價幾乎都是負面的。在高中時曾記得聽老師說過,在學習中國近代史的時候,袁世凱一上場就給人一個“叛徒”的印象,甚至連慈禧老佛爺都曾經怒斥他是一個首鼠兩端的小人。因為當時他曾背叛光緒等而向榮祿告密,致使誅殺慈禧的陰謀敗露,導致戊戌六君子血賤菜市口,康梁逃往外國避難,103天的戊戌變法如曇花一現,所有這些,都不能不說與袁世凱有著直接關係了。
儘管從某些的角度來看,他的確是一個首鼠兩端的小人,但是,在我心目中,袁世凱還是個能夠審時度勢的能人。甚至連唐德剛先生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和用歷史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袁世凱這號歷史人物,說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曾將其與曹操相比,我覺得這樣對他的評價也不為過。他與曹操的區別在於曹操最終都沒有稱帝,而袁世凱卻稱帝了。
袁世凱是一個賣身投靠,終其一生的人,它的政治道德就是跟定一個人,他把國家軍隊作為了它的個人的政治資本,先後投靠過李鴻章、榮祿和奕劻等人。
他有李鴻章般的老謀深算,有張之洞和榮祿般的穩重,以至於他能先在李鴻章的手下做事並且得到李鴻章的極力推薦,儘管李鴻章認為他是一個望風使舵的小人;繼而得到榮祿的器重;最後還得到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極力相助。若非袁世凱有正才實幹,他怎能在晚清那個複雜的社會形勢下生存並迅速發展起來呢?
縱觀袁世凱的一生,複雜得像一部政治小說。從他受任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起,可謂是權傾一時啊!直到被攝政王載灃開缺回籍,在老家“修養”垂釣幾年後,辛亥革命正是風靡全國,而清皇朝的統治就處在隨時都可能被攻破的危險處境,這時候隆欲太后和攝政王才想起了手握北洋六鎮軍隊的“垂釣”老翁了。其實載灃恨透袁世凱了,只因為除了袁世凱外沒有人能夠調動那支親手由他自己建立起來的北洋軍罷了,所以載灃才不得不重新啟用袁世凱,然而,袁世凱東山再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載灃這個仇敵,然後再重組內閣。在袁世凱的左右逢源下,他養敵自重,然後再挾清壓孫,找適當的時機通吃兩家,唯我獨尊,造成一個非袁不可的客觀形勢,最終傾向了“民治”這桿秤的一端,成功地勸服了清帝遜位。
清皇朝被推翻了,袁世凱雖然沒有做成民國第一任大總統,但是他畢竟也做了第二任大總統嘛。然而,就在袁世凱的政治之路正處於巔峰的時候,他的悲劇也正從這時候悄無聲息地緩緩地進行著!
面對著剛建立起來的民國政府,困難重重啊,稍有不慎共和政府便有可能會被扼殺在搖籃之中!
“六君子”之首的立憲專家楊度曾經對黃興說過這樣一句話,“搞專憲,有袁無孫,能行;搞共和,有孫無袁,也能行;但是,有孫又有袁,就什麼也搞不成,要想搞的話,那就看誰死在誰的前頭。”從他這句話可以看出,袁與孫就好比磁石的南北極吧,永遠也不可能黏在一起。旁人可以看得如此清楚,那麼袁與孫這兩個當事人對此是如何看的呢?
在《袁氏當國》這本書中講到,袁世凱可是一個老謀深算的政客啊,他哪里不知道一山不能容二虎的道理呢!於是,他為了清除革命党功臣而安排孫中山一個肥缺優差去修鐵路,並要黃興也去助孫搞實業救國,這樣做的原因就是怕孫文在袁世凱的眼底下搗亂,威脅到他的統治地位。畢竟當時孫文的聲望在全國來說是沒有人能與之相比的。
然而,孫文卻天真的去幹他的實業救國,並聲明要建20萬里鐵路的毫無實際的計畫,並遠赴日本考察鐵路的建設。而正在他遠赴日本考察之際,國民黨在國會大選中大敗進步党,進而有望由國民黨重組內閣,而宋教仁此時卻被人暗殺。孫文這時候才清楚地意識到這個袁世凱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啊!儘管當時還不能肯定宋教仁是否真的給袁世凱下令所殺,但他仍然棄民國法治制度於不顧,走上了以槍桿子發動二次革命為宋教仁之死而討袁的路子。其實,這也是袁與孫缺乏法治觀念的緣故啊!
當時有一個記者叫田沫,她在時報上曾刊登過一篇關於三個人剪辮子的文章,而這三個人分別是孫文、黎元洪和袁世凱。文中說到,孫文當時剪辮子的時候是在給“清狗”打得半死的情況下剪的,這顯示了一個革命先行者與封建專制的決裂;而黎元洪是在槍口下被逼無奈的政治抉擇;袁世凱是個名義上的共和主義者,內心卻是傾向專制的熱,他剪辮子是舍魚而取熊掌的政治權衡。
所以,從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孫與袁兩個人政治立場和革命目的的不同,同時也為袁世凱稱帝而身敗名裂而埋下伏筆。
縱袁世凱的一生來看,他的人生是結局是以悲劇而收場的!
假如袁世凱能夠保持做他的民國大總統,而不搞什麼帝制的話,那麼,我想歷史對他的評價就會大大的改觀了。
辛亥那年,許多人紛紛勸進讓他取清而自代,他不聽;後來當上臨時大總統,孫文力主建都南京,忽然北洋嘩變,當時曹錕要讓他以爭大位,他也不聽。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終究使這個老官僚踏上帝制這條死亡之路呢?
袁世凱的悲哀,正在於他被人給利用和欺騙了!
其一,以楊度為主的這個六人幫對袁世凱稱帝的最後決定還是起著很大的影響的。楊度是憲政專家,發對共和,在他的誘導下,袁世凱還真以為全國人民都支持他稱帝呢!本來對皇帝有很濃厚的興趣他,經楊度這一誘導,心裏就更加是癢癢的。
其二,袁克定欺父誤國。袁克定唆使丫鬟說看見袁世凱睡著的時候有一條龍在他的身上;袁克定還親自拿假的順天報紙和泰晤士報來假傳消息說列強支援其改變國體稱帝,於是也就將其父拖入了糞坑了。
其三,還有那個美國呆書生古德偌吧,他的一篇《共和與君主論》就曾為帝制派所利用,給帝制鋪了一條平平的道路呢!
所以,總的來說袁世凱也是被別人利用了啊,悲哉!
正如唐德剛先生在書上也這樣描述,“袁世凱縱然想做個真正的民主大總統,不但他本人無此智慧條件,他所處的時代也沒有實行民治的社會基礎。他如要回頭搞帝王專制,甚至搞君主立憲,這些形式在當時的中國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所以,這段歷史是必然的,只不過這個歷史的擔子是落在了袁世凱這個悲劇性的人身上罷了。
袁世凱的悲哀是捲入了一個他不能改變的形勢以致終讓歷史所遺棄,而孫文也就可以勉強地說正是因為他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而比袁世凱幸運。民初那個爛攤子是誰也收拾不了的,而袁世凱卻偏偏要踏這趟渾水,歷史選擇了袁世凱來踏這趟渾水,這也是歷史的偶然了,同時也是袁世凱的一個悲哀!
假如袁世凱安安分分地終老于民國大總統的寶座上,那麼,我想他也不至於被後人唾駡如斯了!
《袁氏當國》這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中國轉型的問題。例如,唐內閣不出三個月便壽終正寢也是一個轉型的問題;出現“議員並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的現象,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了科舉的替代品了,入黨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這也是一個轉型的問題;還有如公開審判,也是一個由專制向法制的轉型問題等等。然而,中國民初採取美國模式的共和政體是一項很複雜的社會文化轉型問題,是“知難行亦不易”的。在中國社會文化從“帝制”轉向“民治”的轉型啟蒙期中,全國大多數人都是“民智未開”,因此,以上所凸顯的轉型期中的歷史問題也就不足為怪了。

- selina
- 2013/6/28 12:40:42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袁世凱,他不是第二任。孙中山是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虽然看LZ发的帖很“非主流”,不过也算是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人了。

- wei5359704
- 2013/6/29 7:12:00
得道者多助,得民心者得天下

- 凄夜雪
- 2013/6/30 0:29:42
难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人需要有一颗真诚的心,与忠诚的心

- 麦布兜
- 2013/6/30 9:21:12
个人的确认为袁世凯是识时务者....可能你会认为袁世凯出卖了康梁集团,所以就说他不真诚、不忠心....的确,从这个角度看袁世凯的确是不真诚、不忠心,但是这些“忠心”只是愚忠!忠,在先秦时期,是具有原始民主意识形态的,而不是今天的“愚忠”,在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古人对“忠”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他们不认为一定要忠于国君,例如,范睢一个人就掌管了六国相印,死士豫让“为知之者死”,这些都不是愚忠,因为具有民主的意识形态。但是到了秦以后,中央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时候,加上韩非的一些“朕即国家”、“臣子忠于国君是天经地义”、“国君与臣子关系是一种利益相交的关系,一个臣子一旦投其主,就等于一只狗那样必须终生为其主人服务那样,如果投靠他人,就被说成事背叛”.....等等,岳飞的愚忠,正是这种思想的“杰出代表”....乃至今天,这种思想,充斥在中华大地之上,严重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并指导着我们的行为规范.....
难道袁世凯不告密,康梁和光绪就可以顺利并成功实施他们的变法了吗?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袁世凯不忠于康梁,说明他不像岳飞那样愚忠;他也不忠于慈禧,也不忠于李鸿忠和张之洞....他唯一忠于的人是他自己.....跟着形势走,难道就有错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叔孙通这个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叔孙通说这些起义军只不过是一群狗啊,鼠啊之辈,根本就不用担心,然而他却在秦二世疏于防范的时候溜出了咸阳,然后相继投靠了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归附于刘邦,数次择木而栖。大家都知道,刘邦深受法家思想影响,而对儒家是一种鄙视的态度,当然晚年后他的思想是改变了一些...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刘邦是鄙视儒生的...他曾经将儒生的帽子拿来撒尿!而叔孙通他是一个儒者,而且很懂得礼制。但是在他服侍刘邦期间,他是不穿儒服,而穿楚服。等到刘邦登基后,刘邦与群臣饮酒发觉了礼制的重要性,于是叔孙通趁机进言,建议制定朝礼,赢得刘邦的欢心,而在改易太子的风波中,他却以死相谏,使刘邦改变初衷,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所以,难道说袁世凯因时势的变化而投向他人,就说他是一个叛徒并且至今都得留下被人唾骂的恶名吗?他的不愚忠难道有错吗?况且,有清朝的封建专制到康梁的君主专制也是要一个过渡期间,而且要有很多条件因素,谁敢说当时就已经有了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有这样的土壤吗?
难道袁世凯不告密,康梁和光绪就可以顺利并成功实施他们的变法了吗?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袁世凯不忠于康梁,说明他不像岳飞那样愚忠;他也不忠于慈禧,也不忠于李鸿忠和张之洞....他唯一忠于的人是他自己.....跟着形势走,难道就有错了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叔孙通这个人?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后,叔孙通说这些起义军只不过是一群狗啊,鼠啊之辈,根本就不用担心,然而他却在秦二世疏于防范的时候溜出了咸阳,然后相继投靠了项梁、楚怀王、项羽,最后归附于刘邦,数次择木而栖。大家都知道,刘邦深受法家思想影响,而对儒家是一种鄙视的态度,当然晚年后他的思想是改变了一些...但是纵观他的一生,刘邦是鄙视儒生的...他曾经将儒生的帽子拿来撒尿!而叔孙通他是一个儒者,而且很懂得礼制。但是在他服侍刘邦期间,他是不穿儒服,而穿楚服。等到刘邦登基后,刘邦与群臣饮酒发觉了礼制的重要性,于是叔孙通趁机进言,建议制定朝礼,赢得刘邦的欢心,而在改易太子的风波中,他却以死相谏,使刘邦改变初衷,维护了国家的稳定.....
所以,难道说袁世凯因时势的变化而投向他人,就说他是一个叛徒并且至今都得留下被人唾骂的恶名吗?他的不愚忠难道有错吗?况且,有清朝的封建专制到康梁的君主专制也是要一个过渡期间,而且要有很多条件因素,谁敢说当时就已经有了实施君主立宪制的基础?有这样的土壤吗?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