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 eltooo LV.排长
- 2012/8/27 4:31:11
古时出门远行,须祭祖,尔后取道。今人已摒弃了繁文缛节,也不再相信这些五迷三道的仪式。若临岔口迷津,现代人乖巧地竖起了路标,因循着仪器,变得不再盲目和迟疑。可面对人生歧路,古今之人内心的盘桓无计,却是相通的。
我要演绎的是毕业的伤词,可总想嘶吼出壮士登程的豪曲来。在这样的挣扎中,提笔犹举方鼎,踟蹰蹀躞之下罩着一头雾水。于是,只好从远处谈起。我所膜拜的盲人作家博尔赫斯向世人展示过一座“迷宫”——《小径分岔的花园》。小说中“我”来到中国,在彭氏的后花园里,见证和领悟了什么是真正的迷宫。这座迷宫指向的是彭氏家族口耳相传的一部大书。它启示着读者,书的叙述与呈现是唯一的,而读者的切入路径将在不同地方分岔。每一个岔口,决定迷宫的每一种走法,也决定行走者在迷宫中的命运。博尔赫斯告诉读者,人生和故事的迷宫一样,是有多种可能的。大学于我,已是夕阳末日,可人生于我,才是晨岚初起。在大学的行程尽头,来不及决断前程的行者们,已无可奈何地被推向大学的出口。一个出口总是毗邻着另外的入口。大学之后我们将面临岗位竞争,面临安家立业。人的一生都陷在周而复始的出入之中。
做完关于迷宫的比附,对于我这个钟爱电影的人,觉得大学生活比成电影也是如此投契。大四正如电影的尾声。疑云散尽,真相大白,角色序数登场,人物皆有归宿。当荧幕静止时,好的电影会让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在进入这部题名《大学》的电影之前,生涩的我在中学时代阅读了无数影评。我被《大学》吸引,被打动,然后孜孜以求,终于牟取到入场券。当真的落坐在荧幕前观赏它时,思绪却精鹜八极,一时心神涣散,醒过神来,高潮消退,已只能把玩最后的尾声。我不想离场,不愿离去,还想倒回去看消逝的影像,可电影已经终了,灯光大亮,退场的人群将我裹挟而出。我们该明晓:人生不能重映。大学值得我们从第一幕开始投入。
设若生活是部纪实的电影,这一幕的镜头会对准三月的天宇。阴沉时宛如傅抱石的浓墨山水,晴朗时则似一条洗净泛白的蓝巾。晌午的暖阳会敷热枯燥的皮肤,会晒出一身的细汗。出到门外,春光点绿了几处草甸,也扎染出三两片新叶。从湖上侧身而过的和风,仍让人从头到脚地感到凉意。虽则是暖春,心底却大有“春风更比朔风寒”的凉意。我只顾低了头慢慢地走,夹一颗白沙,走在阒寂的湖边,有时拣一处向阳的草堆,放下身体,远望逶迤的龙山,或绕着湖堤,穿过校园,默默打量拥着书朝教学楼赶的路人,常常会在铃声中失落地靠近文科楼,这时心中会堵满刚被切割的青草末屑的味道。
这样的节令,本该让人放松,恣纵地消受春光。可一站到太阳底下,四下张望,就会感觉自己像个戎马倥偬的老兵,回望这铁打的营盘,心里满是对四年韶光似水流走的喟叹。鼻根里悠悠转出一声唏嘘,这时的我特别渴望朝着日头呐喊。喊什么呢?大学殆尽,青春散场,可人还得朝前生长,人生嘛。落寞是无济于事的,活着是身不由己的。我遽然想起了这么一句口号:“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是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喊出来的。他从故乡喊到了古巴,喊遍了拉美,声声啼喊里沸腾着切的热血。1968年春天,法国巴黎学生曾将它印在游行示威的T恤上,挂在激情讲演时喋喋不休的嘴巴边,引以向现实宣战,激励伙伴们正视现实,忠于理想,锻造新的人生。这句话曾像旗帜一样,引领了一代人。而今天,我们缺失的正是有力的精神导引。从大学走出去,我们需要建立高亢的奋斗信念,去拼争,撕咬,去战斗,建立功勋,去谈好爱情,实现人生的至高价值。
当我们无法超越也无法挽救什么时,只好低下头尥起脚跟,刨动坚硬的生活,然后像解放古巴的战士一样义无返顾地杀奔出去!念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我要演绎的是毕业的伤词,可总想嘶吼出壮士登程的豪曲来。在这样的挣扎中,提笔犹举方鼎,踟蹰蹀躞之下罩着一头雾水。于是,只好从远处谈起。我所膜拜的盲人作家博尔赫斯向世人展示过一座“迷宫”——《小径分岔的花园》。小说中“我”来到中国,在彭氏的后花园里,见证和领悟了什么是真正的迷宫。这座迷宫指向的是彭氏家族口耳相传的一部大书。它启示着读者,书的叙述与呈现是唯一的,而读者的切入路径将在不同地方分岔。每一个岔口,决定迷宫的每一种走法,也决定行走者在迷宫中的命运。博尔赫斯告诉读者,人生和故事的迷宫一样,是有多种可能的。大学于我,已是夕阳末日,可人生于我,才是晨岚初起。在大学的行程尽头,来不及决断前程的行者们,已无可奈何地被推向大学的出口。一个出口总是毗邻着另外的入口。大学之后我们将面临岗位竞争,面临安家立业。人的一生都陷在周而复始的出入之中。
做完关于迷宫的比附,对于我这个钟爱电影的人,觉得大学生活比成电影也是如此投契。大四正如电影的尾声。疑云散尽,真相大白,角色序数登场,人物皆有归宿。当荧幕静止时,好的电影会让观众久久不愿离去。在进入这部题名《大学》的电影之前,生涩的我在中学时代阅读了无数影评。我被《大学》吸引,被打动,然后孜孜以求,终于牟取到入场券。当真的落坐在荧幕前观赏它时,思绪却精鹜八极,一时心神涣散,醒过神来,高潮消退,已只能把玩最后的尾声。我不想离场,不愿离去,还想倒回去看消逝的影像,可电影已经终了,灯光大亮,退场的人群将我裹挟而出。我们该明晓:人生不能重映。大学值得我们从第一幕开始投入。
设若生活是部纪实的电影,这一幕的镜头会对准三月的天宇。阴沉时宛如傅抱石的浓墨山水,晴朗时则似一条洗净泛白的蓝巾。晌午的暖阳会敷热枯燥的皮肤,会晒出一身的细汗。出到门外,春光点绿了几处草甸,也扎染出三两片新叶。从湖上侧身而过的和风,仍让人从头到脚地感到凉意。虽则是暖春,心底却大有“春风更比朔风寒”的凉意。我只顾低了头慢慢地走,夹一颗白沙,走在阒寂的湖边,有时拣一处向阳的草堆,放下身体,远望逶迤的龙山,或绕着湖堤,穿过校园,默默打量拥着书朝教学楼赶的路人,常常会在铃声中失落地靠近文科楼,这时心中会堵满刚被切割的青草末屑的味道。
这样的节令,本该让人放松,恣纵地消受春光。可一站到太阳底下,四下张望,就会感觉自己像个戎马倥偬的老兵,回望这铁打的营盘,心里满是对四年韶光似水流走的喟叹。鼻根里悠悠转出一声唏嘘,这时的我特别渴望朝着日头呐喊。喊什么呢?大学殆尽,青春散场,可人还得朝前生长,人生嘛。落寞是无济于事的,活着是身不由己的。我遽然想起了这么一句口号:“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是阿根廷人切.格瓦拉喊出来的。他从故乡喊到了古巴,喊遍了拉美,声声啼喊里沸腾着切的热血。1968年春天,法国巴黎学生曾将它印在游行示威的T恤上,挂在激情讲演时喋喋不休的嘴巴边,引以向现实宣战,激励伙伴们正视现实,忠于理想,锻造新的人生。这句话曾像旗帜一样,引领了一代人。而今天,我们缺失的正是有力的精神导引。从大学走出去,我们需要建立高亢的奋斗信念,去拼争,撕咬,去战斗,建立功勋,去谈好爱情,实现人生的至高价值。
当我们无法超越也无法挽救什么时,只好低下头尥起脚跟,刨动坚硬的生活,然后像解放古巴的战士一样义无返顾地杀奔出去!念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 songmoses
- 2012/8/27 10:10:16
班霸髮貼,不得不頂

- kelejia
- 2012/8/28 5:46:57
不知道这些文字的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 lena_sll
- 2012/8/28 17:57:27
不知道这些文字的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念一句: 人之将走其言也善,似乎不太合适,
再来一句: 文有多真人就有多真,似乎也不太妥贴
还是应该说人如其文好些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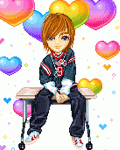
- 张泽华
- 2012/8/29 8:35:40
毕业,无论你怎么诉说都不过分。。。

- nuskin
- 2012/8/30 3:03:37
加油吧
刀兄
刀兄

- bjdfw
- 2012/8/30 13:43:21
"大学于我,已是夕阳末日,可人生于我,才是晨岚初起"
--------------我喜欢这句
到外面走走,就不会在伤春时节唏嘘了
P.S. 我也很喜欢LZ的附图风格...呵呵
--------------我喜欢这句
到外面走走,就不会在伤春时节唏嘘了
P.S. 我也很喜欢LZ的附图风格...呵呵

- as1985
- 2012/8/31 5:12:50
很强大,洋洋洒洒,颇有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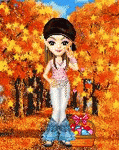
- weihanxiao
- 2012/8/31 23:21:15
毕业于我... 貌似还有一小段时间...叹叹...
时间过得真TMD快啊....
一眨眼,就老了........
时间过得真TMD快啊....
一眨眼,就老了........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