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伤逝

- 吉虎佛儿 LV.连长
- 2012/5/8 22:38:05
爱的伤逝
——从《伤逝》看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的反目
《伤逝》是鲁迅众多作品中唯一一篇是关于爱情的文章。离经叛道一起冲破世俗束缚的子君和涓生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了,但最终还是在日益变得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两人还是分离了。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把《伤逝》解读为鲁迅的爱情观,烂漫与现实的冲突使得鲁迅对刚刚升起希望的迟到爱情深怀忧虑,透过涓生的日记反映出鲁迅对爱情和生活的冷静思考。这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说法。但是我从众多研究鲁迅的资料中发现,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突然反目而且反目得这么彻底却很少有人去分析。
《伤逝》公开发表后,周作人曾公开表示《伤逝》其实就是为他而写的。这一说法一出来就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周作人是汉奸。但是我觉得,作为鲁迅的弟弟,又曾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对于鲁迅内心深处的想法,周作人应该是可以体会到一二的。所以周作人认为《伤逝》是为自己而写是有其可信之处的。
1925年10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全文是:“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时隔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写道:“《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我以为:在儿女情爱之外,《伤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叛逆与庸常之间无法调和的尖锐冲突,这正是兄弟反目的关键所在,或许对此周作人心领神会。
当初子君和涓生一道叛离世俗束缚,异常坚决地蔑视各方的阻滞;可短暂自由的狂喜后,越来越紧逼的生存压力使双方都意识到:业已失去了实现自己价值的生存土壤。风刀霜剑严相逼,子君在无望的日子里逐渐变得琐屑和悲观,涓生也最终难以忍受庸常带来的失落和茫然,最终吐露真实、试图寻找新的焕发生命之路。
整篇小说的基调是沉郁、灰冷的: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
远地!……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
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周作人和鲁迅都曾是叛逆者,共同对陈腐的传统发起过激烈的挑战。五四以后周作人越来越贴近逃遁,偏于雅斋闲适的情调,甚至在对待侵略等问题上不再有洞察是非的锐气;在对残酷现实的充分认识后,鲁迅仍然选择了彻底的叛逆,独自站在主流的逆面,发出在暗夜里厚重的悲鸣。
不难想象,兄弟俩骨子里叛逆和庸常的矛盾形成了表面上为家事、小节的口角争执,迟早有激化的导火线。在兄弟反目的种种是非中,细节往往掩盖了两个文化巨子真实的精神距离。
这正是兄弟俩反目的关键所在,两个人在对待世界观、人生观的巨大差别让两人发生了很大的分歧,生活上的家事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相信两个兄弟不至于因为钱上的事情而发生这么大的分歧,况且鲁迅还是很爱他的弟弟的。据许寿棠回忆,当年兄弟俩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一天周作人偷懒,不想再做下去的时候,鲁迅立刻过去给了周作人脑上一拳。幸亏旁边的友人帮忙劝开了。可见鲁迅对亲人是爱之深,责之切。
当年,林语堂一度和鲁迅关系很好,亲如战友。但最好两人还是成为了敌人。因为两人在文学上的观点很不一样。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有人说反目因为鲁迅的天性不宽容,可能没有透过犀利的文风看到他赤子般的爱。
尽管受过种种误解和伤害,鲁迅对宫竹心、廖立峨、郭沫若等小人还是有过近乎迂阔的爱和宽容,真是侠骨柔肠、让我都有些替他遗憾。在爱和宽容方面,鲁迅有时表现得或许近乎童稚。
反目后很久,鲁迅还嘱咐三弟建人提醒周作人在对日本的态度上要自省自爱,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个“连自己的手都不懂自己的足”二弟。从长久来看,二弟对鲁迅的伤害意味着什么?是论敌用以讥笑的口实?还有朝朝暮暮晦暗的心绪,对唤醒国人魂灵希冀的幻灭,选择叛逆后的旷古孤独。
鲁迅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要求朋友、亲人都很高,眼里掺不得沙子。所以才会导致和朋友和亲人反目,而这样对鲁迅自己伤害也很大。《伤逝》当中就有这样的反映。一篇《伤逝》还是体现了鲁迅对兄弟间反目的原由来。
PS:《伤逝》一文真的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从《伤逝》看鲁迅兄弟俩的反目只是一个方面,我还试图从《伤逝》中分析鲁迅的情爱观。有兴趣的各位也说来看看~~
——从《伤逝》看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的反目
《伤逝》是鲁迅众多作品中唯一一篇是关于爱情的文章。离经叛道一起冲破世俗束缚的子君和涓生自由地结合在一起了,但最终还是在日益变得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两人还是分离了。学术界普遍的观点是把《伤逝》解读为鲁迅的爱情观,烂漫与现实的冲突使得鲁迅对刚刚升起希望的迟到爱情深怀忧虑,透过涓生的日记反映出鲁迅对爱情和生活的冷静思考。这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说法。但是我从众多研究鲁迅的资料中发现,鲁迅和二弟周作人的突然反目而且反目得这么彻底却很少有人去分析。
《伤逝》公开发表后,周作人曾公开表示《伤逝》其实就是为他而写的。这一说法一出来就遭到了大家的反对。为什么呢?因为周作人是汉奸。但是我觉得,作为鲁迅的弟弟,又曾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对于鲁迅内心深处的想法,周作人应该是可以体会到一二的。所以周作人认为《伤逝》是为自己而写是有其可信之处的。
1925年10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一首诗,题目就是《伤逝》。全文是:“我走尽迢递的长途,渡过苍茫的灰土,作徒然的话别,因为她那命运的女神忽而给予又忽而收回,已经把你带走了。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时隔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写道:“《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我以为:在儿女情爱之外,《伤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叛逆与庸常之间无法调和的尖锐冲突,这正是兄弟反目的关键所在,或许对此周作人心领神会。
当初子君和涓生一道叛离世俗束缚,异常坚决地蔑视各方的阻滞;可短暂自由的狂喜后,越来越紧逼的生存压力使双方都意识到:业已失去了实现自己价值的生存土壤。风刀霜剑严相逼,子君在无望的日子里逐渐变得琐屑和悲观,涓生也最终难以忍受庸常带来的失落和茫然,最终吐露真实、试图寻找新的焕发生命之路。
整篇小说的基调是沉郁、灰冷的:
“然而现在呢,只有寂静和空虚依旧,子君却决不再来了,而且永远,永
远地!……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
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周作人和鲁迅都曾是叛逆者,共同对陈腐的传统发起过激烈的挑战。五四以后周作人越来越贴近逃遁,偏于雅斋闲适的情调,甚至在对待侵略等问题上不再有洞察是非的锐气;在对残酷现实的充分认识后,鲁迅仍然选择了彻底的叛逆,独自站在主流的逆面,发出在暗夜里厚重的悲鸣。
不难想象,兄弟俩骨子里叛逆和庸常的矛盾形成了表面上为家事、小节的口角争执,迟早有激化的导火线。在兄弟反目的种种是非中,细节往往掩盖了两个文化巨子真实的精神距离。
这正是兄弟俩反目的关键所在,两个人在对待世界观、人生观的巨大差别让两人发生了很大的分歧,生活上的家事只是一个导火线而已。相信两个兄弟不至于因为钱上的事情而发生这么大的分歧,况且鲁迅还是很爱他的弟弟的。据许寿棠回忆,当年兄弟俩一起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一天周作人偷懒,不想再做下去的时候,鲁迅立刻过去给了周作人脑上一拳。幸亏旁边的友人帮忙劝开了。可见鲁迅对亲人是爱之深,责之切。
当年,林语堂一度和鲁迅关系很好,亲如战友。但最好两人还是成为了敌人。因为两人在文学上的观点很不一样。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有人说反目因为鲁迅的天性不宽容,可能没有透过犀利的文风看到他赤子般的爱。
尽管受过种种误解和伤害,鲁迅对宫竹心、廖立峨、郭沫若等小人还是有过近乎迂阔的爱和宽容,真是侠骨柔肠、让我都有些替他遗憾。在爱和宽容方面,鲁迅有时表现得或许近乎童稚。
反目后很久,鲁迅还嘱咐三弟建人提醒周作人在对日本的态度上要自省自爱,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这个“连自己的手都不懂自己的足”二弟。从长久来看,二弟对鲁迅的伤害意味着什么?是论敌用以讥笑的口实?还有朝朝暮暮晦暗的心绪,对唤醒国人魂灵希冀的幻灭,选择叛逆后的旷古孤独。
鲁迅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要求朋友、亲人都很高,眼里掺不得沙子。所以才会导致和朋友和亲人反目,而这样对鲁迅自己伤害也很大。《伤逝》当中就有这样的反映。一篇《伤逝》还是体现了鲁迅对兄弟间反目的原由来。
PS:《伤逝》一文真的可以写出很多东西来,从《伤逝》看鲁迅兄弟俩的反目只是一个方面,我还试图从《伤逝》中分析鲁迅的情爱观。有兴趣的各位也说来看看~~

- 白露为霜
- 2012/5/9 0:55:09
从伤逝看未婚同居的结局,警戒现在的年轻人。。。切勿乱动。。

- gameland
- 2012/5/9 19:42:06
谁谁谁动了我的奶酪

- 沐春风
- 2012/5/10 9:37:04
谁谁谁动了我的奶酪
谁谁谁动了我的内裤

- xiaoyuankk
- 2012/5/11 1:25:32
我晕~~谁谁谁动了我的评价

- 酷酷鲁
- 2012/5/11 14:25:47
谁谁谁动了我的内裤
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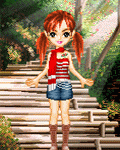
- 范小欣
- 2012/5/12 3:31:42
:~7 12把作业发上来了啊

- hxhxdod
- 2012/5/12 20:33:28
没什么好发的,就弄了个作业上来分享下。

- yummy
- 2012/5/13 11:40:55
作业啊………………………………
赞扬了
赞扬了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