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而奋力的大学四年(上)----也谈我的前半生系列

- xc456321 LV.连长
- 2011/7/20 7:29:53
悲凉而奋力的大学四年(上)----也谈我的前半生系列之n+7
1978年5月,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厂子里的工友和领导,怀着说不清的心情,走进了天天都进的大学校门。这样说,是因为我家就住在校內,不过此前我并非在读学生而是教工家属而已。
既然又进了学校当学生,就要像个学生的样子。再说父亲曾在此担任了几十年的系主任,那我总不能太丟人吧。
刚入学几天,教外语的廖老师把我们四五个后进来的走读生(都是广州考生,初时都住在家里)叫到他家门口小院座谈,主要是让我们自报各人的英文水平。我记得梁某说他会翻译,陈孙二位说能读能写;比我高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叶大姐则说得较谦,大意也与陈孙差不多;唯有我直说只会读字母表,因为中学的代数几何中用过,而五年中学读的却是俄语。廖老师最后叮嘱我要加把劲赶上去,其实他与我母亲是多年同事,我看得出来他的叮咛是好意中带着七八分担心。
由于进校已经比别人晚了近两个月,差不多就要进入第一学期的期中考了----怎么办?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别人在这两个月学的东西先补上,那就只有从时间上先把这两个月挤出来。我把拉下的功课全部审视了一番,发觉数学和力学由于以前有些基础故差距还不算太大,主要是英文基本是文盲。有了判断,便有计划地分配时间。好在这几个月儿子还在他妈的肚子里,除了每天傍晚到对面省拖拉机厂门口公交车站等着接老婆之外,还没有给我添太大的麻烦。倒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学会了在马路边上看书的本领:不管眼前有多少车马行人,都不会影响我看书的集中程度。谁知到了快近期末考试时,突然发高烧请了两天假,辅导我们力学的汪老师亲自上门问我有没有困难、是否需要额外的帮助等等。汪老师对待学生的关怀,我永远难忘;他在学生作业上密密麻麻的批改和讨论,既保存在我的作业本上,也长留在我的心中。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大学老师的教学态度大致均如此,与我现在看到的新老师风格反差太大了。一学期下来,艰苦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全班三十多人中大概排在三四名左右吧。尤其是力学得了99分,也使我觉得没有愧对汪老师。汪老师当时在系里算个小卒子,现在已是教授博导了,看来严谨治学还是做学问的根本。英语没有考试而是考查,也顺利过了一关。接下来的整个暑假,我知道自己面前是什么样的路,所以每天与未放假时无异,无非看书做习题,还有就是做家务接送老婆等。这时大妹已经结婚,五人同住两房一厅,妈妈当正厅长,小妹偶尔回来则当副厅长。而我仍还是家中的第一把手厨师,妈妈到油锅烧热了就叫我:“快来炒牛肉片!” 因为当时只有我才能炒得最嫩。
第二学期快开始时,老婆身子很沉重了。有次下车被人一推掉下来,把全家都吓得不轻,幸亏儿子扒得结实没掉下来。九月初,把老婆送回北京路娘家住,因距离准备生产的中山一院比较近。我只好跑来跑去,但也帮不上什么忙,纯粹一个干着急。某晚半夜老婆作动,两个小舅子用事先借来的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次晨我才赶去医院。不久,儿子就出生了。那时不让探访住院产妇及初生儿,但喜可从窗外探头看到了妻儿。老婆状有尚可。小孩儿则红红的脸,头发又多又长,使我最小的小舅子骄傲地说:“我外甥的‘的水’几长!” 那时刚好时兴留长鬓角的港式头发,鬓角粤语称为“的水”也。老婆的五十六天产假期间,有妈妈帮忙,学习和家庭之间还算不太慌乱,只是小孩半夜里常常要吃奶或撒尿,弄得本来就会失眠的我更缺睡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挨过来的,每晚大概平均能睡个二至三小时就不错了,可上课看书作业等却精神抖擞。五十六天一过,老婆便每天带儿子“进城”,先把儿子放在一位退休阿姨处,再去单位工作;中途按时去喂奶,中午常到娘家去蹭餐。我作为一个男人,更作为丈夫和父亲,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又能作些什么呢? 每月除了老婆44.50元工资之外,妈妈在孙子出生后常给我们塞点钱,岳家则不收老婆的饭钱,后来学校又给了我12元的助学金。一小家三口人靠着这些过日子,我这腰杆挺得直吗? 即使以后毕业了,也还不知道出路如何呢。不过想多了也无益,抓紧时间埋头苦干吧。仍然是每周六天傍晚到马路边看书接老婆儿子,但时时见老婆背着满头满脸通红的儿子从人缝中挤出14路车,心里哪能不泛起一阵阵辛酸啊。周日中午,为了让老婆有受儿子干扰睡一好觉,常抱着那小子挑荫处走走,或到无午休习惯的老友黎家呆呆。不过,此时在美国和香港的舅舅舅母以及妈妈在加拿大的同学给我们寄来了不少婴儿用品,大大地缓解了我们的窘迫状况。好不容易熬过电磁学、分子物理、政治经济学以及最要命的英语考试,这第二学期在班里还能排个五六名左右吧。
第三学期刚开始不久,大妹的儿子也出生了,现在是七人常住在约50平米的房子里。不到睡觉时,两个小鬼吵吵闹闹,时而友好时而争吵;到了夜里,吃奶撒尿之声彼起此伏。儿子将近一岁时,突然患了腹泻,水泻时象开了龙头的水一样射出来。当时正流行“二号病(即霍乱)”,学校里有几栋学生宿舍都给隔离封闭起来了。我们被吓得半死,赶紧把小孩送往越秀区儿童医院住院。看着那幼小的生命在吊针、吃炭粉以及种种检验等一系列折磨中挣扎,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儿子并不是霍乱,而医生的手段还是奏效了。经过这段惊吓,就没有儿子再送到阿姨处,留在家里找来我们小时的保姆娇姐帮助妈妈带小孩。
待到儿子一岁半,便替他到学校附设的幼儿园报名入托。谁知园长冷冰冰地说: “我们招收的是教工子女,接收学生的孩子还没有先例!” 其实我们也知道,入托小孩中有许多是教工的孙子,而我的父母都是本校教工,但人家就是不听你的解释,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只好去央求她已经当了副校长的中学同学(中学未毕业即去了延安),该同学让人事处长和幼儿园联系。后来我们按处长之嘱再去报名时,园长却又满脸笑容地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 总之历经艰辛,总算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
此后不久,我为了学习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搬到学生宿舍去住,因为小孩已不吃奶,半夜里的事就减少了很多;二是很少在家看书作业,将学习大本营迁到老友黎家狭长屋子里端的一个房间,因为这里很少干扰。
在宿舍里,我睡在同样常常失眠的石弟弟上床,并在床上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凳子,还在蚊帐顶上开了个洞引入了一盏电灯。这是为了晚上自习时躲避蚊子叮咬用的。睡觉时,就把凳子放到桌子上,而双腿就从桌子两边的腿缝穿过。
石弟和我是同一中专不同班同学,事先并不认识,因他在灯泡厂的“电光源”班,我在钟厂的“轻工机械”班。他人极聪明且刻苦,又有大把时间到图书馆刨书练习等,学业水平比我高一截; 而我只能在温习功课完成作业的基础上再略看一点参考书。虽然我们二人都苦于失眠,可每到考试前一夜,石弟每隔半小时便去厕所小便一次,还唉声叹气,弄得我也彻夜不眠。但第二天考试,二人状态的区别就很大了----石弟抗不住失眠的压力,通常只能考出七八成水准; 而失眠则对我好象毫无影响,除了把自已真正懂的东西全拿到手外,还凭推测多取几分。这样一比较下来,水平高的石弟往往还比我少几分。
就这样,在前两年的学习中,总算维持了班上的中上水平,不至于太丢脸----因为当时每学期考试结束后,全级成绩按高低排名贴在系的公告栏中,人人包括学生老师都能一目了然的啊。记得榜首总是我班的高考状元,前几名也是我们的班友,但倒数几名同样也是我们班的人。这样的排名常令我纳闷: 我们班(专业)不是全省录取分数最高的二专业之一吗? 难道基础好的人学出来的成绩不应该高于基础差者吗? 这其中的道理我是毕业后多年才悟出来的,不过那是后话了。
现在回想起来,黎家的小房间是我在四年大学学习生涯中获益最多之处。这里很少有人打搅,我往往可以连续三四个小时不出房门一步,看完这一门功课又看另一门。当然也有休息的时间,例如屋子前端常有黎友或其弟的朋友在打麻将,偶尔他们中的某人要上厕所或暂有某事,便叫我去顶上,最多也就二十分钟;又或者有时看书累了,也和黎友下上一盘半小时以内的高速围棋。
至于后两年的事,现在一时也写不出来,只好待慢慢边忆边写吧!
1978年5月,依依不舍地辞别了厂子里的工友和领导,怀着说不清的心情,走进了天天都进的大学校门。这样说,是因为我家就住在校內,不过此前我并非在读学生而是教工家属而已。
既然又进了学校当学生,就要像个学生的样子。再说父亲曾在此担任了几十年的系主任,那我总不能太丟人吧。
刚入学几天,教外语的廖老师把我们四五个后进来的走读生(都是广州考生,初时都住在家里)叫到他家门口小院座谈,主要是让我们自报各人的英文水平。我记得梁某说他会翻译,陈孙二位说能读能写;比我高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叶大姐则说得较谦,大意也与陈孙差不多;唯有我直说只会读字母表,因为中学的代数几何中用过,而五年中学读的却是俄语。廖老师最后叮嘱我要加把劲赶上去,其实他与我母亲是多年同事,我看得出来他的叮咛是好意中带着七八分担心。
由于进校已经比别人晚了近两个月,差不多就要进入第一学期的期中考了----怎么办? 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把别人在这两个月学的东西先补上,那就只有从时间上先把这两个月挤出来。我把拉下的功课全部审视了一番,发觉数学和力学由于以前有些基础故差距还不算太大,主要是英文基本是文盲。有了判断,便有计划地分配时间。好在这几个月儿子还在他妈的肚子里,除了每天傍晚到对面省拖拉机厂门口公交车站等着接老婆之外,还没有给我添太大的麻烦。倒是在这段时间内,我学会了在马路边上看书的本领:不管眼前有多少车马行人,都不会影响我看书的集中程度。谁知到了快近期末考试时,突然发高烧请了两天假,辅导我们力学的汪老师亲自上门问我有没有困难、是否需要额外的帮助等等。汪老师对待学生的关怀,我永远难忘;他在学生作业上密密麻麻的批改和讨论,既保存在我的作业本上,也长留在我的心中。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大学老师的教学态度大致均如此,与我现在看到的新老师风格反差太大了。一学期下来,艰苦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全班三十多人中大概排在三四名左右吧。尤其是力学得了99分,也使我觉得没有愧对汪老师。汪老师当时在系里算个小卒子,现在已是教授博导了,看来严谨治学还是做学问的根本。英语没有考试而是考查,也顺利过了一关。接下来的整个暑假,我知道自己面前是什么样的路,所以每天与未放假时无异,无非看书做习题,还有就是做家务接送老婆等。这时大妹已经结婚,五人同住两房一厅,妈妈当正厅长,小妹偶尔回来则当副厅长。而我仍还是家中的第一把手厨师,妈妈到油锅烧热了就叫我:“快来炒牛肉片!” 因为当时只有我才能炒得最嫩。
第二学期快开始时,老婆身子很沉重了。有次下车被人一推掉下来,把全家都吓得不轻,幸亏儿子扒得结实没掉下来。九月初,把老婆送回北京路娘家住,因距离准备生产的中山一院比较近。我只好跑来跑去,但也帮不上什么忙,纯粹一个干着急。某晚半夜老婆作动,两个小舅子用事先借来的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次晨我才赶去医院。不久,儿子就出生了。那时不让探访住院产妇及初生儿,但喜可从窗外探头看到了妻儿。老婆状有尚可。小孩儿则红红的脸,头发又多又长,使我最小的小舅子骄傲地说:“我外甥的‘的水’几长!” 那时刚好时兴留长鬓角的港式头发,鬓角粤语称为“的水”也。老婆的五十六天产假期间,有妈妈帮忙,学习和家庭之间还算不太慌乱,只是小孩半夜里常常要吃奶或撒尿,弄得本来就会失眠的我更缺睡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挨过来的,每晚大概平均能睡个二至三小时就不错了,可上课看书作业等却精神抖擞。五十六天一过,老婆便每天带儿子“进城”,先把儿子放在一位退休阿姨处,再去单位工作;中途按时去喂奶,中午常到娘家去蹭餐。我作为一个男人,更作为丈夫和父亲,心中自然不是滋味,但又能作些什么呢? 每月除了老婆44.50元工资之外,妈妈在孙子出生后常给我们塞点钱,岳家则不收老婆的饭钱,后来学校又给了我12元的助学金。一小家三口人靠着这些过日子,我这腰杆挺得直吗? 即使以后毕业了,也还不知道出路如何呢。不过想多了也无益,抓紧时间埋头苦干吧。仍然是每周六天傍晚到马路边看书接老婆儿子,但时时见老婆背着满头满脸通红的儿子从人缝中挤出14路车,心里哪能不泛起一阵阵辛酸啊。周日中午,为了让老婆有受儿子干扰睡一好觉,常抱着那小子挑荫处走走,或到无午休习惯的老友黎家呆呆。不过,此时在美国和香港的舅舅舅母以及妈妈在加拿大的同学给我们寄来了不少婴儿用品,大大地缓解了我们的窘迫状况。好不容易熬过电磁学、分子物理、政治经济学以及最要命的英语考试,这第二学期在班里还能排个五六名左右吧。
第三学期刚开始不久,大妹的儿子也出生了,现在是七人常住在约50平米的房子里。不到睡觉时,两个小鬼吵吵闹闹,时而友好时而争吵;到了夜里,吃奶撒尿之声彼起此伏。儿子将近一岁时,突然患了腹泻,水泻时象开了龙头的水一样射出来。当时正流行“二号病(即霍乱)”,学校里有几栋学生宿舍都给隔离封闭起来了。我们被吓得半死,赶紧把小孩送往越秀区儿童医院住院。看着那幼小的生命在吊针、吃炭粉以及种种检验等一系列折磨中挣扎,我们真不知如何是好。幸亏儿子并不是霍乱,而医生的手段还是奏效了。经过这段惊吓,就没有儿子再送到阿姨处,留在家里找来我们小时的保姆娇姐帮助妈妈带小孩。
待到儿子一岁半,便替他到学校附设的幼儿园报名入托。谁知园长冷冰冰地说: “我们招收的是教工子女,接收学生的孩子还没有先例!” 其实我们也知道,入托小孩中有许多是教工的孙子,而我的父母都是本校教工,但人家就是不听你的解释,有什么办法呢? 母亲只好去央求她已经当了副校长的中学同学(中学未毕业即去了延安),该同学让人事处长和幼儿园联系。后来我们按处长之嘱再去报名时,园长却又满脸笑容地说: “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 总之历经艰辛,总算把儿子送进了幼儿园。
此后不久,我为了学习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搬到学生宿舍去住,因为小孩已不吃奶,半夜里的事就减少了很多;二是很少在家看书作业,将学习大本营迁到老友黎家狭长屋子里端的一个房间,因为这里很少干扰。
在宿舍里,我睡在同样常常失眠的石弟弟上床,并在床上放了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凳子,还在蚊帐顶上开了个洞引入了一盏电灯。这是为了晚上自习时躲避蚊子叮咬用的。睡觉时,就把凳子放到桌子上,而双腿就从桌子两边的腿缝穿过。
石弟和我是同一中专不同班同学,事先并不认识,因他在灯泡厂的“电光源”班,我在钟厂的“轻工机械”班。他人极聪明且刻苦,又有大把时间到图书馆刨书练习等,学业水平比我高一截; 而我只能在温习功课完成作业的基础上再略看一点参考书。虽然我们二人都苦于失眠,可每到考试前一夜,石弟每隔半小时便去厕所小便一次,还唉声叹气,弄得我也彻夜不眠。但第二天考试,二人状态的区别就很大了----石弟抗不住失眠的压力,通常只能考出七八成水准; 而失眠则对我好象毫无影响,除了把自已真正懂的东西全拿到手外,还凭推测多取几分。这样一比较下来,水平高的石弟往往还比我少几分。
就这样,在前两年的学习中,总算维持了班上的中上水平,不至于太丢脸----因为当时每学期考试结束后,全级成绩按高低排名贴在系的公告栏中,人人包括学生老师都能一目了然的啊。记得榜首总是我班的高考状元,前几名也是我们的班友,但倒数几名同样也是我们班的人。这样的排名常令我纳闷: 我们班(专业)不是全省录取分数最高的二专业之一吗? 难道基础好的人学出来的成绩不应该高于基础差者吗? 这其中的道理我是毕业后多年才悟出来的,不过那是后话了。
现在回想起来,黎家的小房间是我在四年大学学习生涯中获益最多之处。这里很少有人打搅,我往往可以连续三四个小时不出房门一步,看完这一门功课又看另一门。当然也有休息的时间,例如屋子前端常有黎友或其弟的朋友在打麻将,偶尔他们中的某人要上厕所或暂有某事,便叫我去顶上,最多也就二十分钟;又或者有时看书累了,也和黎友下上一盘半小时以内的高速围棋。
至于后两年的事,现在一时也写不出来,只好待慢慢边忆边写吧!

- oneshow
- 2011/7/20 10:27:03
在大学同学网上看到一位同学刘某在谈足球,勾起我的一段回忆。快毕业的那学期,中山大学物理系“体育代表团”访问暨南大学物理系,当然有足球,好象还有乒乓球等。足球上场者我只记得有我和同班的赖某和从汕头市队来的邻班陈某,具体还有谁就要找回照片来看了。打的是十一人的大场。
陈某名不虚传,百米是11"5,而且球很粘脚,便带着球在前场左冲右突,无奈总有两三个对方后卫纠缠着,很难起脚,勉强的几脚射门也被没收。虽然场面我们占优,但总无法打破僵局。上半时就这样过去了,下半时也是就这样快过完了,眼看就要握手言和。
这时,我方正是攻势,全队大举压上,我打的中卫也压到中圈附近,我们的一名前锋不知是谁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叫对方守门员没收了。对方守门员看我方后防较空虚,而他们也有两名前锋和我方两三名后卫大致并排在中圈附近,便大脚往前吊球。正当那球快要落在我前面几米处时,我身为防守中坚,心知这球一旦过了我的头实在就等于给对方前锋单刀直入了,于是疾步向前迎球冲上去,左腿飞起一脚,目标并不明确,或是解围或是吊给自己的前锋,总之是不让它过我的头就行。谁知正好踢中了部位,而我的左右两腿从小练得力度相当,那球便在离地五六米的空中划出一道平缓的弧线直飞向对方球门。对方守门员肯定没想到从近五十米外飞来的球有多少劲道,便打算让球在面前几米处落地后反弹进自己怀中。哪里料得到球门前地面不平,许是落地的一剎那球碰到了一个泥疙瘩而突然跳高了,球就从弯腰接球的守门员头顶上翻进门去了,之后很快便完场。
中大物理系VS暨大物理系,1:0,结束。后来拍了照片,中大的人全是蓝色T裇,只有我一个人是蓝背心。改日找出那照片挂上来瞧瞧。未知赖某等当时队友尚记得此一幕否? 哈哈!
大学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 我记得我们家中还是用一台14英寸拼装黑白电视机看球的. 那场在香港进行的中国对朝鲜的世界杯小组预选赛中, 90分钟内2:2打平. 后来的加时赛中, 先是王向东40多米外劲射, 球紧贴草皮急窜向球门右侧, 对方守门员扑了一下没挡远, 陈熙荣插上补入, 3:2. 接着古广明象泥鳅一样在对方禁区盘带连过几人后射入. 4:2, 肯定出线了吧?! 我妈都激动得哭了.
后来中国队却被沙特和新西兰算计了: 沙特有意让新西兰5球, 令中国队和新西兰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苏指导当时也没有经验, 让全队解散了五个月, 后仅集中几天便去新西兰打附加赛, 输掉了. 场上具体的人和事只记得大概, 不知有错否?
陈某名不虚传,百米是11"5,而且球很粘脚,便带着球在前场左冲右突,无奈总有两三个对方后卫纠缠着,很难起脚,勉强的几脚射门也被没收。虽然场面我们占优,但总无法打破僵局。上半时就这样过去了,下半时也是就这样快过完了,眼看就要握手言和。
这时,我方正是攻势,全队大举压上,我打的中卫也压到中圈附近,我们的一名前锋不知是谁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叫对方守门员没收了。对方守门员看我方后防较空虚,而他们也有两名前锋和我方两三名后卫大致并排在中圈附近,便大脚往前吊球。正当那球快要落在我前面几米处时,我身为防守中坚,心知这球一旦过了我的头实在就等于给对方前锋单刀直入了,于是疾步向前迎球冲上去,左腿飞起一脚,目标并不明确,或是解围或是吊给自己的前锋,总之是不让它过我的头就行。谁知正好踢中了部位,而我的左右两腿从小练得力度相当,那球便在离地五六米的空中划出一道平缓的弧线直飞向对方球门。对方守门员肯定没想到从近五十米外飞来的球有多少劲道,便打算让球在面前几米处落地后反弹进自己怀中。哪里料得到球门前地面不平,许是落地的一剎那球碰到了一个泥疙瘩而突然跳高了,球就从弯腰接球的守门员头顶上翻进门去了,之后很快便完场。
中大物理系VS暨大物理系,1:0,结束。后来拍了照片,中大的人全是蓝色T裇,只有我一个人是蓝背心。改日找出那照片挂上来瞧瞧。未知赖某等当时队友尚记得此一幕否? 哈哈!
大学的最后一年即1981年, 我记得我们家中还是用一台14英寸拼装黑白电视机看球的. 那场在香港进行的中国对朝鲜的世界杯小组预选赛中, 90分钟内2:2打平. 后来的加时赛中, 先是王向东40多米外劲射, 球紧贴草皮急窜向球门右侧, 对方守门员扑了一下没挡远, 陈熙荣插上补入, 3:2. 接着古广明象泥鳅一样在对方禁区盘带连过几人后射入. 4:2, 肯定出线了吧?! 我妈都激动得哭了.
后来中国队却被沙特和新西兰算计了: 沙特有意让新西兰5球, 令中国队和新西兰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苏指导当时也没有经验, 让全队解散了五个月, 后仅集中几天便去新西兰打附加赛, 输掉了. 场上具体的人和事只记得大概, 不知有错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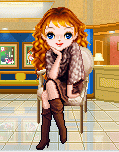
- 小紫草
- 2011/7/21 9:17:02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 不幸的家庭却各不相同. 某大文豪用类似字句作为其一部长篇的首句. 其实他笔下的一个卡列宁家庭本身就包含了这两类家庭的缩影, 而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单个家庭也莫不如此. 我三年级时, 就经历了一段第二类家庭的日子----儿子患上了百日咳.
有段时间, 幼儿园儿子班里许多小朋友都咳嗽, 他也不例外. 老师和阿姨(保育员)都说: 班里现在象有一群小公鸡, 这只未呜完那只又打啼. 老婆、我妈和我都着急: 这孩子不停咳嗽, 咳得脸红脖子粗且上气不接下气, 眼看著一天天瘦着虚弱着下去, 而且无论看多少次医生都不管用, 咋办? 更要命是他半夜里也这样, 又怕影响仅一板之隔的妈妈及妹妹两夫妇和小外甥. 每晚我唯有几小时几小时地抱着他在黑暗中眼睁睁地静待天明, 让老婆养神以腾出白天弄他. 只有这样他的咳嗽才基本止住, 一放下又不行了.
实在受不了既不睡觉又要上课、复习、看书、作业的折磨, 更心疼日渐不成人形的儿子. 孩子已有些懂事, 每晚睡前自己仔细掖好被子还说“一受凉就又会咳嗽了, 要小心”----这种小大人的话是受了多少苦的孩子才会说的啊! 听了都觉揪心.
当时也没有多少钱可买书, 便到北京路科技书店蹭看各种医书, 好在当时蹭看书的人多得很, 许多人也如我一样都带着笔记本在抄录, 也不致令我太尴尬. 对照儿子病状发现很象百日咳了; 一天突然又从蹭看的中华大药典中发现所载百日咳药仅三种, 即鹭鶿涎、猪胆丸及另一种已忘名之药. 于是就近到北京路健民药房打听, 仅有其中一种即武汉肉联厂出品的猪胆丸, 而且非常便宜, 不到一元一瓶. 当晚, 如获至宝的我立即拿回去仔细按份量(说明书上说毒性很大, 从几个月到几岁都有严格的份量区别)给孩子吃下去, 并告诉他这是治咳的特效药.
许是真让我碰对了, 再加上心理暗示, 当晚就让全家都睡了一个几个月没有过的安稳觉. 此后坚持用药, 病情不断好转, 几个月后终告痊癒. 至于是不是真的患过百日咳, 也就没心思再追究了. 总之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我这回有点体会了. 我家这一段不走运的日子就这样渡过了, 而每晚仅一至二小时睡眠似乎也并未对我的学习造成太大不良影响.
本来想接着写下去, 一时又有些別的贱事缠身, 暂此搁笔一段吧.
有段时间, 幼儿园儿子班里许多小朋友都咳嗽, 他也不例外. 老师和阿姨(保育员)都说: 班里现在象有一群小公鸡, 这只未呜完那只又打啼. 老婆、我妈和我都着急: 这孩子不停咳嗽, 咳得脸红脖子粗且上气不接下气, 眼看著一天天瘦着虚弱着下去, 而且无论看多少次医生都不管用, 咋办? 更要命是他半夜里也这样, 又怕影响仅一板之隔的妈妈及妹妹两夫妇和小外甥. 每晚我唯有几小时几小时地抱着他在黑暗中眼睁睁地静待天明, 让老婆养神以腾出白天弄他. 只有这样他的咳嗽才基本止住, 一放下又不行了.
实在受不了既不睡觉又要上课、复习、看书、作业的折磨, 更心疼日渐不成人形的儿子. 孩子已有些懂事, 每晚睡前自己仔细掖好被子还说“一受凉就又会咳嗽了, 要小心”----这种小大人的话是受了多少苦的孩子才会说的啊! 听了都觉揪心.
当时也没有多少钱可买书, 便到北京路科技书店蹭看各种医书, 好在当时蹭看书的人多得很, 许多人也如我一样都带着笔记本在抄录, 也不致令我太尴尬. 对照儿子病状发现很象百日咳了; 一天突然又从蹭看的中华大药典中发现所载百日咳药仅三种, 即鹭鶿涎、猪胆丸及另一种已忘名之药. 于是就近到北京路健民药房打听, 仅有其中一种即武汉肉联厂出品的猪胆丸, 而且非常便宜, 不到一元一瓶. 当晚, 如获至宝的我立即拿回去仔细按份量(说明书上说毒性很大, 从几个月到几岁都有严格的份量区别)给孩子吃下去, 并告诉他这是治咳的特效药.
许是真让我碰对了, 再加上心理暗示, 当晚就让全家都睡了一个几个月没有过的安稳觉. 此后坚持用药, 病情不断好转, 几个月后终告痊癒. 至于是不是真的患过百日咳, 也就没心思再追究了. 总之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我这回有点体会了. 我家这一段不走运的日子就这样渡过了, 而每晚仅一至二小时睡眠似乎也并未对我的学习造成太大不良影响.
本来想接着写下去, 一时又有些別的贱事缠身, 暂此搁笔一段吧.

- nuskin
- 2011/7/21 15:34:44
说句老实活:我这四年悲凉而奋力的大学生活并非出于自愿,不过现在回顾却自以为极有价值.
其实我的一生好象都由不得自己安排或选择----除了自己挑了个老婆.
幼稚园、小学因家住中山大学当然只能是大学附属的了.
初中想考华附,但体弱被母亲斥之曰"你怎能寄宿"就替我定为广州六中了.
高中又想考华附,但班主任对父亲说:"你儿子平时成绩我们心中有数,考失手了我们也会录的(我初二升初三时肝炎没考年考也升级了)."父亲就替我仍定了六中.其中班主任家访还有点趣事:时已开始有人上山下乡.班主任对父曰"你的仔如考不上高中,你会否让他去农村?"老豆居然大言不惭:"我嘅仔点会考唔到高中呢?无可能,虎父点会生犬子?"这话让偷听的我出了一口气(对班主任看不起我的怨气),也让我觉肩上之担重于泰山.
高中毕业去农村,去否及去向均由工宣队贴在牆上的大红榜决定,无人可说一个"不"字.
回城后以高中毕业生身份读中专,也是因为无工可打,借姐夫之力读中专权当曲线入厂之路.
手表厂并非我首选,本想入轻工研究所.但父老病且母亦病,被迫选距中山大学最近之工厂了.
厂里干得好好的,提拔是迟早(也许马上)的事.可77高考来了,老妈一声令下,由不得不考.
大学毕业分配,有家口之累容不得我选择北京的研究单位.权衡再三,只好选择当自己从小做梦也没想过的"老师"这条一辈子之路.
87年,副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拿一张表喜滋滋地把我从上课讲台上拉下來说:"我好不容易替你争取到一个考出国的名额.快填了这表,中午12点前还给我,好赶着交上去!"那时已是十点多了.她口气及时限容不得与家里讨论,就这样苦读英文(才学过二年)→考EPT→培训德文一年→去西德留学.我当时虽不太愿出国(原因很多,也许后述)但不敢违抗,因慑于上司之威,有感于上司之关怀;又考虑许多本校毕业生都在备考或已考上,自己是重点大学分来的,说不考好象太没面子,只好半将就屈从了.
当然,从父母、姐夫、上司以及"组织上"都是好意,之后事实也证实他们指的路子不错.可总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一辈子的路都由别人安排,真不甘心.
所以儿子大学毕业后,愿意干啥我就让他自谋生路吧,别让他象我那样了.
今晚羊城晚报一篇"一丈三尺六----布票的故事"使我和老婆引起共鸣.1960年起,每人发布票一丈三尺六,即一年可购布总量为一丈三尺六寸.作为结婚时用光了二人布票置办床上用品,最后被亲人发现没窗帘,笑道"打赤膊"(光膀子叫人看见了);后竭尽全力替她们补救.
我儿子1978年出生时,恰逢小妹要到武汉读大学,也用尽了所有渠道汇集来可用的布.后来用香港亲戚寄来的呈纱布状尿布做了儿子的小棉被套,用街上不须票的、走线的处理毛巾接起来做了儿子的毛巾被.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会笑.可晚报上作者关于孩子出生后缺布的一段话发人深醒,兹节录如下:"有智者说,如果生存成了你生活的第一需要,那你不会有什么烦恼.此言千真万确.试想为买布票打折的布排长龙是何等可怜可哀?其实我们当时却全无哀怜之感,因为都在为生存挣扎,哪有闲心理会悲哀不悲哀可怜不可怜!事实也如此,那时日子饥馑却没有烦恼.说得准确些,就是没有什么想头.上班、下班,就着工资票证吃饭穿衣,周而复始.日子就这样毫无欲念、波澜不惊地流淌."
啊,这是我们那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而我比作者更凄凉一点的是: 我是个没有工资却有儿子的大学生. 嘿! 啊!
其实我的一生好象都由不得自己安排或选择----除了自己挑了个老婆.
幼稚园、小学因家住中山大学当然只能是大学附属的了.
初中想考华附,但体弱被母亲斥之曰"你怎能寄宿"就替我定为广州六中了.
高中又想考华附,但班主任对父亲说:"你儿子平时成绩我们心中有数,考失手了我们也会录的(我初二升初三时肝炎没考年考也升级了)."父亲就替我仍定了六中.其中班主任家访还有点趣事:时已开始有人上山下乡.班主任对父曰"你的仔如考不上高中,你会否让他去农村?"老豆居然大言不惭:"我嘅仔点会考唔到高中呢?无可能,虎父点会生犬子?"这话让偷听的我出了一口气(对班主任看不起我的怨气),也让我觉肩上之担重于泰山.
高中毕业去农村,去否及去向均由工宣队贴在牆上的大红榜决定,无人可说一个"不"字.
回城后以高中毕业生身份读中专,也是因为无工可打,借姐夫之力读中专权当曲线入厂之路.
手表厂并非我首选,本想入轻工研究所.但父老病且母亦病,被迫选距中山大学最近之工厂了.
厂里干得好好的,提拔是迟早(也许马上)的事.可77高考来了,老妈一声令下,由不得不考.
大学毕业分配,有家口之累容不得我选择北京的研究单位.权衡再三,只好选择当自己从小做梦也没想过的"老师"这条一辈子之路.
87年,副系主任兼教研室主任拿一张表喜滋滋地把我从上课讲台上拉下來说:"我好不容易替你争取到一个考出国的名额.快填了这表,中午12点前还给我,好赶着交上去!"那时已是十点多了.她口气及时限容不得与家里讨论,就这样苦读英文(才学过二年)→考EPT→培训德文一年→去西德留学.我当时虽不太愿出国(原因很多,也许后述)但不敢违抗,因慑于上司之威,有感于上司之关怀;又考虑许多本校毕业生都在备考或已考上,自己是重点大学分来的,说不考好象太没面子,只好半将就屈从了.
当然,从父母、姐夫、上司以及"组织上"都是好意,之后事实也证实他们指的路子不错.可总没有我说话的份儿.一辈子的路都由别人安排,真不甘心.
所以儿子大学毕业后,愿意干啥我就让他自谋生路吧,别让他象我那样了.
今晚羊城晚报一篇"一丈三尺六----布票的故事"使我和老婆引起共鸣.1960年起,每人发布票一丈三尺六,即一年可购布总量为一丈三尺六寸.作为结婚时用光了二人布票置办床上用品,最后被亲人发现没窗帘,笑道"打赤膊"(光膀子叫人看见了);后竭尽全力替她们补救.
我儿子1978年出生时,恰逢小妹要到武汉读大学,也用尽了所有渠道汇集来可用的布.后来用香港亲戚寄来的呈纱布状尿布做了儿子的小棉被套,用街上不须票的、走线的处理毛巾接起来做了儿子的毛巾被.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会笑.可晚报上作者关于孩子出生后缺布的一段话发人深醒,兹节录如下:"有智者说,如果生存成了你生活的第一需要,那你不会有什么烦恼.此言千真万确.试想为买布票打折的布排长龙是何等可怜可哀?其实我们当时却全无哀怜之感,因为都在为生存挣扎,哪有闲心理会悲哀不悲哀可怜不可怜!事实也如此,那时日子饥馑却没有烦恼.说得准确些,就是没有什么想头.上班、下班,就着工资票证吃饭穿衣,周而复始.日子就这样毫无欲念、波澜不惊地流淌."
啊,这是我们那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而我比作者更凄凉一点的是: 我是个没有工资却有儿子的大学生. 嘿! 啊!

- huanglei88
- 2011/7/22 11:26:15
1.当大学教师最不可能的就是请假,一般是除非快死了才请假的.如果请了假,要经历很复杂的程序补课.我从教廿多年未请过一次.
2.我无法滿30年教龄,故到60退拿97%,提前退拿95%,差异趋于零.补贴没有是真,但我去翻译三五天就拿回来了,无需辛苦一个月.即使坐在家里,消费不高,也够花了.
3.从助教到教授都不用坐班,我仅副教授而已.但最自由或最不自由则任由你自己挑:你可以从天亮到半夜都在实验室,也可以除上课外啥也不干.但实际上高校教师压力极大:每年考核,不做"作家"搞出几篇文章或一两本书来,一年先受黄牌警告,二年就高职低聘,三年就除名.这些苦处校外的人是不易了解的了.
2.我无法滿30年教龄,故到60退拿97%,提前退拿95%,差异趋于零.补贴没有是真,但我去翻译三五天就拿回来了,无需辛苦一个月.即使坐在家里,消费不高,也够花了.
3.从助教到教授都不用坐班,我仅副教授而已.但最自由或最不自由则任由你自己挑:你可以从天亮到半夜都在实验室,也可以除上课外啥也不干.但实际上高校教师压力极大:每年考核,不做"作家"搞出几篇文章或一两本书来,一年先受黄牌警告,二年就高职低聘,三年就除名.这些苦处校外的人是不易了解的了.

- almdzkj
- 2011/7/23 1:01:25
1."学校可以不去,书一定要多读"绝难完全苟同----除天才者外,不入大学的人基本上极难接触更说不上有扎实专业基础以至肯定无法成材.书要多读那是必然.
"学校的教育制度是对人性的最大扼杀,老师天天捧着三流学者编的教材,孜孜不倦地背呀背的,能教什么好学生"----有一定道理.我有用三流学者编的教材,也有用一流学者编的教材,以及国外新出的原版有威信教材;大体上每年即使是同一门课也不断加入当今世界最新发展趋势的介绍,却未知能否教出什么好学生.
当然我心里明白,今后真能成材者仅十份之一二.但不断扩招,学生入学水准我以为比不上我入大学当年未能考入中专者----我却非巧妇,能作此巧妇都作不成之无米炊否?且生师比不断扩大,教师每人面对学生人数渐多----我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这些同学的全部问题(大多数学生志不在学故提不出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或完全不提,仅5%能提出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有多少精力去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准?更兼屋漏逢夜雨----搬大学城,天天路上疲于奔命,人不死都不错了,晚上回来累得眼都睁不开,我有几条命可以象以前一样钻研呢?对我的要求能现实些否?
所以我以为,不上大学绝大多数走不上成才之路.但人人上大学,大学绝对就是绝路.中国教育制度之差,办学水平之劣,学生数与老师数比之大,世界绝无仅有.除了无法可想无他路可走者以及有法发财升官者,有良心教师都不太想留下去故在大学中的比例在递降,那是无疑的或铁定的趋势了.
2."上学奋力,即向三流学者低头,打死我,也不上学"----有一点理,也有无理至极之处:上大学奋力不完全等同于向三流学者低头;学校中确有大批三、四、五、六流学者,但绝非100%均如此.
打死你你也不上大学,那1000个这样的你中有2个成材应算很高比例了,还未知能不达到千分之二呢.
至于"三流学者和老师们的驼背,不打碎是不行的.好老师全不在,坏老师一大把"则实难苟同:难道全部大学老师均是三流且均驼背都须打倒?一二流者一个都无?这论调与文革时提倡的"打倒一切学术权威"如出一辙,其不合理性或合理性均毫无讨论价值.
"不上学,去图书馆去书店,和学院里的学生老师绝交",个人认为绝非走向真理之路.至少从与大学、图书馆、书店、大学教师学生交流之后将其内涵或意见去伪存真,才有走上寻求真理之路的可能.
我的个人愚见一定是管窥而已.
最好商榷.
1.学校可以不去,读一定要多读。学校的教育制度是对人性的最大扼杀,老师天天捧着三流学者编的教材,孜孜不倦地背呀背的,能教什么好学生。所以,不上学,才是成才之路。人人上学,学校就是绝路。中国教育制度之差,办学水平之劣,世界罕见。
2.上学奋力,即向三流学者低头,打死我,也不上学。三流学者和老师们的驼背,不打碎是不行的。好老师全不在,坏老师一大把。能不上学就不上,去图书馆,去书店,和学院里的学生老师绝交,才能走向真理之路。
"学校的教育制度是对人性的最大扼杀,老师天天捧着三流学者编的教材,孜孜不倦地背呀背的,能教什么好学生"----有一定道理.我有用三流学者编的教材,也有用一流学者编的教材,以及国外新出的原版有威信教材;大体上每年即使是同一门课也不断加入当今世界最新发展趋势的介绍,却未知能否教出什么好学生.
当然我心里明白,今后真能成材者仅十份之一二.但不断扩招,学生入学水准我以为比不上我入大学当年未能考入中专者----我却非巧妇,能作此巧妇都作不成之无米炊否?且生师比不断扩大,教师每人面对学生人数渐多----我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这些同学的全部问题(大多数学生志不在学故提不出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或完全不提,仅5%能提出有讨论价值的问题)?有多少精力去思考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准?更兼屋漏逢夜雨----搬大学城,天天路上疲于奔命,人不死都不错了,晚上回来累得眼都睁不开,我有几条命可以象以前一样钻研呢?对我的要求能现实些否?
所以我以为,不上大学绝大多数走不上成才之路.但人人上大学,大学绝对就是绝路.中国教育制度之差,办学水平之劣,学生数与老师数比之大,世界绝无仅有.除了无法可想无他路可走者以及有法发财升官者,有良心教师都不太想留下去故在大学中的比例在递降,那是无疑的或铁定的趋势了.
2."上学奋力,即向三流学者低头,打死我,也不上学"----有一点理,也有无理至极之处:上大学奋力不完全等同于向三流学者低头;学校中确有大批三、四、五、六流学者,但绝非100%均如此.
打死你你也不上大学,那1000个这样的你中有2个成材应算很高比例了,还未知能不达到千分之二呢.
至于"三流学者和老师们的驼背,不打碎是不行的.好老师全不在,坏老师一大把"则实难苟同:难道全部大学老师均是三流且均驼背都须打倒?一二流者一个都无?这论调与文革时提倡的"打倒一切学术权威"如出一辙,其不合理性或合理性均毫无讨论价值.
"不上学,去图书馆去书店,和学院里的学生老师绝交",个人认为绝非走向真理之路.至少从与大学、图书馆、书店、大学教师学生交流之后将其内涵或意见去伪存真,才有走上寻求真理之路的可能.
我的个人愚见一定是管窥而已.
最好商榷.
1.学校可以不去,读一定要多读。学校的教育制度是对人性的最大扼杀,老师天天捧着三流学者编的教材,孜孜不倦地背呀背的,能教什么好学生。所以,不上学,才是成才之路。人人上学,学校就是绝路。中国教育制度之差,办学水平之劣,世界罕见。
2.上学奋力,即向三流学者低头,打死我,也不上学。三流学者和老师们的驼背,不打碎是不行的。好老师全不在,坏老师一大把。能不上学就不上,去图书馆,去书店,和学院里的学生老师绝交,才能走向真理之路。

- 奶油聒心
- 2011/7/23 16:10:23
话说我那儿子出生时,物质匮乏.好在在港的外婆和两对舅父舅母鼎力相助,远在美国的一对舅父母亦一味支持,老妈子出银出力;而外家几个海员包括泰山大人和两个小舅子常帶回各种物品,泰水大人让我老婆和那小子免费午餐.
不过令我最谅讶的是母亲的同学也是我父母的结婚介绍人陈姨妈,与我本人就非亲非故了.她先生解放前是国立中山大学物理系主任即我老头子的上司,后移台湾任教,旋赴新加坡南洋大学好象是任校长吧,退休后定居加拿大以在子女近旁生活.她给我儿子寄来的东西时令我目瞪口呆,而且连打税钱都一併寄来.有次寄来一罐奶粉,竟然粒粒似化肥尿素那样的小珠子,大小完全一致;用水一冲即化而无需搅拌.
没有这些亲朋支撑,我老婆44.50元哪里真能养活三口人呢?
不过令我最谅讶的是母亲的同学也是我父母的结婚介绍人陈姨妈,与我本人就非亲非故了.她先生解放前是国立中山大学物理系主任即我老头子的上司,后移台湾任教,旋赴新加坡南洋大学好象是任校长吧,退休后定居加拿大以在子女近旁生活.她给我儿子寄来的东西时令我目瞪口呆,而且连打税钱都一併寄来.有次寄来一罐奶粉,竟然粒粒似化肥尿素那样的小珠子,大小完全一致;用水一冲即化而无需搅拌.
没有这些亲朋支撑,我老婆44.50元哪里真能养活三口人呢?

- hubin026
- 2011/7/24 9:31:08
希望能看到下部
ps:现在论坛怎么要求字数了?本来上面就是我要说的话,结果现在有要写这样一堆废话,无奈啊!
ps:现在论坛怎么要求字数了?本来上面就是我要说的话,结果现在有要写这样一堆废话,无奈啊!

 校园资讯
校园资讯